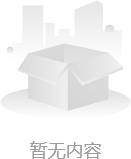那年夏天,满脸稚气的我跨出卫校的大门,满怀期待和好奇迈进医院,成为了一名母亲口中“打针(输液)发药”的护士,在简短的入职培训后正式开启了我的“打针”之旅。治疗室内一排铝盒子,里面躺着一个个灭菌后的吊筒,将玻璃瓶内的无菌液体倒入2L大小的广口玻璃吊筒中,用玻璃注射器将药物稀释后打入吊筒内,盖上盖子,吊筒下面的橡胶管连接钢针,为病人输液。每次输液,我们都要注意避免铝盒、吊筒等之间发生碰撞,“咣咣”的噪声是其次,最怕的是发生破碎,导致药液浪费。使用完后,我们要把注射器、吊筒仍然装在铝盒里,与消毒供应室工人进行清点交接,放在箩筐里,用扁担挑到供应室进行清洗、消毒、灭菌,出生农村的我惊奇的发现,运送各种物品,箩筐、扁担在医院里仍大有用武之地。在那个时候的输液中,我们经常会遇到家属喊“老师,病人在打抖”,我们经常判断,发生输液反应了,立即予以对症处理,在业务学习、“三基”考试中,输液反应是常考内容。反复使用、多次高温灭菌的玻璃注射器在使用中时有碎裂,曾经有一个老师在配药时发生注射器碎裂,右手掌心被割得鲜血淋漓,去外科缝了好几针。那时候,“一针见血”是对护士工作能力的极大肯定。那是1995年,那年我19岁,风华正茂,祖国46岁,正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阔步前进。
那一年,我读到一篇文章,作者是一位到新加坡出差的政府人员,因患急病到当地医院住院治疗,文中写到与本地住院的差别,其中写道有一种针可留在血管内使用一周而不必每天扎针,痛苦极大的减少(作者没有写明是留置针)。我至今记得那种无比羡慕的心情。那时,我们刚刚用上了一次性输液器和钢针,想到扎针困难时,4、5个护士姐妹轮番上阵或者一齐上阵,找手找脚甚至找头部的血管,想到病人病情突变时扎针的紧张心慌,想到小朋友扎针时因疼痛而生的恐惧哭喊,觉得这个针好好啊,我们好久能用上啊。那应该是2000年左右吧,我24岁,祖国51岁。
已经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,留置针进入了中国,然后,慢慢进入了四川,再后来也进入了我们医院,并从手术室慢慢进入了我们各个内科。我也用上了曾经梦想中的输液工具,我不断的练习、不断地摸索,成为了一名扎针的好手。而留置针也不断改进迭代,作为祖国西南省区的一个西南城市,新产品进入我们的临床与东部发达地区的时间差也越来越小。
那一年,我科护理人员首次参加了四川省“静脉输液治疗”的专科护士培训,我们越来越认识到“打针”并不仅仅是“打针”,“一针见血”仅仅只是开始,在输液治疗领域中,如何恰如其分的选择输液工具,如何预防和处理输液相关的并发症,护士都大有可为。我们相继开展了PICC、超声引导下改良赛丁格技术置入PICC、输液港置入与维护等。
那一年,秋高气爽,我去北京参加“静脉输液治疗专科护士培训”,从理论到实践,我的“扎针”之旅如同安上了翅膀。聆听来自北京各大院校、医院业内大咖们的精彩授课,越发体会到输液治疗的进展来自于祖国的日益强大。比如PICC ,上世纪末从国外引进时我们处于绝对落后的地位,在千千万万同行的拼搏下,本世纪初我们在快速地追赶,距离越来越近,到最近几年的学术交流中,我们国家的研究成果让欧美同行频频点头认同。那一年,我41岁,已经不惑之年,我不惑于个人成长来自于科室与医院的平台,更来自于祖国坚强有力地托举。那一年,祖国68岁,正在世界舞台上焕发着越来越夺目的光彩。
近年来,输液治疗实践领域风起云涌,跨学科的合作如火如荼,到今年,我院已经成功开展下肢PICC置入术、上臂输液港置入术,我积极配合完成了全院静脉输液横断面调查,还在积极推动全院置管与维护中心的整合与建立。在祖国70华诞之际,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从建国时的35岁提高到了2018年的77岁,翻了1倍还多。这举世瞩目的成就里面,也有我的一点点微光,我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。20多年来,我从一名对护理工作懵懵懂懂的小姑娘成长为副主任护师,作为一名普通护士,我是全国300余万护理人员中的一员,我所在的医院,是全国近千所三甲医院中的一所,我的经历,我的成长之旅,是全国千千万万各行各业同胞的缩影。
先贤曾说,怎样让一滴水永不干涸,唯一的方法,就是把它溶入大海。怎样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呢?就是投入到伟大祖国的建设中去,为人民健康、为民族复兴、为祖国的八十、九十、百年华诞奋斗!